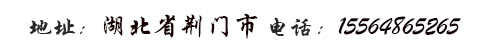读懂米兰middot昆德拉这本高分晦
|
北京中科白颠疯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 点击上方绿标收听音频 文:钰迪丨主播钰迪 小满 《生活在别处》虽然赞誉极高,但却并不好懂,或者说有些观念我并不认同。马尔克斯50多个拉美名字的小说我都读得清晰流畅,但是这个通篇只有雅罗米尔一个名字的书,我却很难挤进作者的思想里。 虽然只是读了两遍,但好像跑了两个月的马拉松一样疲惫。即使是这样,依然对这本书难以割舍。就好像结婚后你总是有无数次想把对方踹下床的决心,但大部分人却还得气消后挽起对方手臂认真走完余生。 那些“眼皮底下”触手可及的人和故事,你出手的时候,他们就瞬间变了模样,成了幻象。我臣服于昆德拉对文字驾驭的功力,也不得不承认又一次被他的书名欺骗。他靠卖梦为生,只是梦里忘了放盐。 书里的每个字看的越清楚,越难以和作者的意识产生耦合。最后,我反而开始质疑我的存在。到底生活应该在别处,还是应该在当下呢?因为好像只有“生活在别处”的我,才能和“此处书中的你”回眸一笑。忽觉半夏花开,唯愿再次沉默。 小说主线围绕“诗人”雅罗米尔的诞生到死去展开,延伸出母亲、革命和诗歌,三个重要视角,每个视角都可以独立成歌,但只有纠缠糅合在一起才是完整饱满的故事。另外还有两个看似“番外篇”的部分独立于这条主线之外——“克萨维尔”和“四十来岁的男人”。 但读到后面你会知道克萨维尔其实就是雅罗米尔,他们彼此互为镜像,而“四十来岁的男人”作为诗人的对立面,在小说结构中展现了一种微妙的套层关系。 一个是如雅罗米尔这样被命运的铁环拉扯的东倒西歪,却不放弃追逐生命的光亮与伟大,意义与澄澈。在现实中满脚泥泞,在理想里一眼花开。 而另一个就是这位“四十来岁的男人”。作者的话形容这两部分嵌套的关系很精妙,很有镜头感:“就仿佛湖中央的楼阁和整个庄园一样。阁楼是独立的建筑,庄园也能离开它而存在;但阁楼的窗户开着,因此庄园里居民的声音总是若隐若现。” 四十来岁的男人从来不追求命运,他认为所有想象的浮华都是对实际感受的折损。他只是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享用命运迎面而来的瞬间。把一切田园牧歌踩在脚下,连倒影的涟漪都狠狠咂干。 你可以说他是小说雅罗米尔的另一个对立面,一个现实生活的旁观者,甚至可以感觉他从文字中忽然起身,坐在了我的身旁,或许他根本也是一个读者。 伴随小满初夏的凉风,我只想静静地和这本书躺一会。我不完全认同它,但是它却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Part01 「我一直觉得,在另一个地方,我的生活会更好——寻找自己」 ▼ 在诗歌的里面是上帝视角,而在诗歌的边上是撒旦的歌唱。 昆德拉试图用颠倒、错乱、虚假、荒诞来成就一种纯粹的文学。他的小说不提供任何认知、判断,就是一种最初和最后的意识胶黏的混沌状态。在“我是别人,还未成为我之前”似乎都是值得所有人大笑一场,再次努力却再也笑不出来的。 “生活、战斗、忍受痛苦、爱。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在别人眼里的他们应该这样做,特别是为了这个原本应当这样,却未能这样的世界。” 诗人母亲的真正生活不是在一地鸡毛、亲情疏离的阁楼上,而是在与画家短暂又激情的私会中;红发女孩的生活也不在诗人变态又幼稚的诗句中,而在中年男人温存又如父爱的臂弯里;雅罗米尔真正的生活也并不在他臆想出的那些自私畸形的爱恋中,不在一辈子都脱离不出的“孤独母爱”中,而在他投身革命那虚妄的狂欢中。在那些纯真感伤心灵的背面,在那些矫揉造作的诗句里面,藏着的是虚伪、自私、懦弱、妄想的真实丑态。 只有错位的人生,才能挤压出欲望的毒疮。 诗人敏感的内心与孱弱的行动撕扯着自我构建的藩篱,这种对现实存在的困惑和主体身份的艰难认同,从童年一直走到成年,越想挣脱越被捆绑,只能在可笑的诗歌里得到喘息,在最后的毁灭中得到重生。 《生活在别处》描写的50年代的捷克,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但是昆德拉说,我们这些还记得的人必须作证:它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激情的时代。 时间向来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在欧洲中世纪,教会垄断了立法权,钟声最早从修道院传出,召唤还未清醒的人们,假装清醒和坚定地去晨祷、弥撒。虔诚的手遮盖的是罪恶的心。但不妨碍他们抒情。 特定时代使不同环境中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释放出来。雅罗米尔是个"邪恶"的人,他在试图直面现实、逃离母爱的道路上,毁灭了情人,也毁灭了自己。但这样的邪恶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所有制度所有时代的每个年轻人身上。 所有的时代都会产生雅罗米尔。他只是个一直试图站在道德高地呐喊,却一直浇灌着人性恶之花的少年。 昆德拉展示了这位富有想象力和激情的年轻诗人一生的心理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的内涵是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雅罗米尔终其一生都在为进入现实世界而努力。他的出生被赋予神秘又神圣的色彩。“诗人诞生的家庭往往都离不开女人的统治,于是诗人穷尽一生的时间在自己的脸上寻找男子汉的特征。” 妈妈始终认为儿子是神童,从小就能把普通的话语通过独特的韵律和抒情方式说出来。在优越感中长大的雅罗米尔,一直觉得精神是高于肉体的,爱情要建立在灵与肉的分离上,才能体现其伟大。所以当他在第一段爱情中受挫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男子气概,怀疑自己一直对女人的欲望停留在脸蛋上,是肤浅和可笑的。 那些所有的爱情、勇敢和激荡都只是存在于诗歌里。他在寻找自己身体男性特征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早已破碎的半张脸。 人必须真实的活着,唯有真实才能触碰到存在。而他的存在只是在一行连一行的诗歌里,在一片接一片的梦境里,诗歌是他逃避真实世界最好的平行空间。在这份虚幻中,他看到A面的懦弱和B面的坚毅,A面的自己总是在现实中长得很快,而B面的人生只能在睡梦里积蓄力量,在现实一碰就碎。 “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在自我欺骗。”但是,我们必须好好活着。 /Part02 「无论诗人怎样奔跑,他还只是个孩子——逃离母爱」 ▼ 母亲和儿子的非正常依恋关系,是儿子悲剧命运的根源。“诗人究竟是在哪里被怀上的呢?”全书第一句话就为雅罗米尔此处的人生定了调,他必须不断奔跑逃离,寻找别处的生活。 雅罗米尔的出生就是失控的。婴儿本来是处于孤独的想象世界,他和妈妈构建的世界是过渡世界,而广阔的社会则是真实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三重世界。健康的母子关系,就是三重世界的依次断裂与重建。但是雅罗米尔的一生都无力从过渡世界看到真实世界的模样。 诗人的妈妈和婴儿最初是共生关系,共享一个自我,无论谁离开谁都是共享自我的死亡。所以把自己对生活和爱情绝对的渴望都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的这位母亲,一开始塑造的和儿子的共生关系就是畸形的。过于旺盛的占有欲,让婴儿一生都在试图切割又总是归顺于母爱的路上连滚带爬,惊怖不已。 母爱像如来佛的手掌,让诗人“人造的一生”的悲剧,总像演也演不好,逃又逃不掉的闹剧。 从诗人的出生,母亲就在违背父亲的意愿。她希望把丈夫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用一个孩子作为纽带紧紧箍牢,让婚姻中死去的爱情,起死回生。但是她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只能靠变态的占有把丈夫越推越远。内心的孤寂和巨大的悲哀,让她选择在儿子身上索取爱的回馈。 儿子从最初对母亲无条件的依恋顺从,到后来的逃离厌恶,但无论奔跑到何处,母亲的影子总是比现实更强大,所以他只能一边试图逃离母亲,又一边不得不寻求母爱。 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一个想把一个塞进尿布,永远占有;一个想把一个裹进尸布,从此消失。 但到最后儿子发现那种令自己恐惧窒息的爱,才是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的爱。而自己为之投入青春时代全部热情的革命,只是充盈着满腔愚昧的虚幻气泡,此起彼伏破碎在诗歌的上空。这份寂静,震耳欲聋。 雅罗米尔不是个低劣的诗人,他只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假巨人”,真实世界的“真矮子”。对“生活在此处”的自己如此不安不满,因此他短暂又矛盾的一生一直在奔跑逃离,最后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他只能在自己的瞭望台上,一次次对现有的生活和真实的自己进行精神背弃,对现实越抵触绝望,对诗歌的庇护越渴望。 “从冥想的王国中被驱逐 我在人群中寻找庇护 我想咒骂 想用它换了我的歌。” 他在四面是镜子的房间,轻声哼唱着自己的诗。那些叮叮当当和镜面碰触的回响,让他知道诗与诗之间,梦和梦这边,都有精神的守望。现实的光越刺眼,镜中的世界就越深沉。在那些诗句唇枪舌战、不分昼夜的舞台,热闹和激情是从来不缺的。只是真实存在的人,不愿意去听到。 诗人在母爱世界中意识不到现实世界的对立,而在诗的幻想中又逃避着这种对立。母亲从小对他的溺爱与霸占,让他在“一元型”共生关系里,很难对社会的多元性繁杂张开双臂。 当后来遇到青春、遇见爱情,雅罗米尔试图切断这份和母亲的过分亲密关系,他不再写诗,也总是希望和母亲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当他意识到母爱变成一种专制的力量限制着他的现实行动时,他已经一辈子都无法逃脱母爱世界所加之于他的束缚。 从母爱世界过渡到诗的世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全部舍弃,也不能彻底逃离。这一切都是真实生活的镜像。一想就有,一碰就没。 母爱是对现实世界的切断,而诗歌成为一种对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诗人从逃离母爱的奔跑中败下阵来,又从诗与现实分裂的隙缝之中滑落下来。 生活离析,今夕何夕。 真正的生活不在场,我们却在世界上热泪成冷眼,热血结成冰。 "而天上却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灯火辉煌的路标,时间分割为一道灿烂的光谱。他无比兴奋地从一道光跳到另一道光,每次都坚信落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自我与现实的对立之中,我们都需要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 为了自由,我们要爱,但决不要爱的束缚。 于是,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美的欣赏,爱不是嘘寒问暖,不是衣食饱暖,爱只是灵魂的颤动,只是心灵的投契。于此-,妈妈对诗人从小到大的病态的呵护和占有是爱吗?诗人对红衣女孩绝对粗暴的统治和霸凌是爱吗? 爱,也许正是愿意为一个人放弃自由的勇气。爱,是为一个人可以向全世界宣战的力量。爱,是为一个人可以愿意一夜长大的决心。 诗人还是个孩子,但是他依然可以去爱。在真实世界里,哪怕爱的拙劣不堪,也好过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争奇斗艳。 /Part03 「生活的别处,只是另一个真实的此处罢了——成全自己」 ▼ 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总以为有希望翘首等待。其实别处的生活只能喂养欲望,却于心灵无益,而珍视当下的生活,才能真的找到自己。 婴儿时期开始逐渐由母体脱离的我们,第一次由“一元关系”进入到“多元社会”,这个时候我们会由一个曾经完全可以靠哭闹掌控的世界,进入到哭闹不止甚至都无人理睬的青春时代。从掌控到失控,对生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lanhuaa.com/mlhjz/8942.html
- 上一篇文章: 心怀雅,行致远在一4班中考表彰会上的
- 下一篇文章: 无锡金桥小学这个10岁小姑娘相当结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