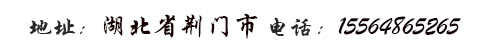常春藤诗丛middot吉林大学卷隆重
|
常春藤诗丛 “常春藤诗丛”之吉林大学卷已于近期问世,这是人天兀鲁思(北京)文化传媒对中国诗歌出版的诗意巨献。该卷主编为李占刚、包临轩,由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郭力家、任白、李占刚、包临轩、苏历铭、伐柯十位诗人诗选构成。权威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从长春、从大学校园出发走向全国,且至今仍在诗坛具有影响力的诗人的成就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面貌。这些诗人所具有的探索、独立、豁达、真挚、清新、空灵、低调、朴素的诗风,构建和丰富了当代诗人的诗学和美学传统。 常春藤诗丛吉林大学卷(10册) 吉林大学卷主编 李占刚包临轩 吉林大学卷作者 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郭力家 任白包临轩李占刚苏历铭伐柯 城市是一座文化盛典,其表层和内里都储藏着大量文化密码,需要有立场、有眼光的发现和解析,将来还可以引入大数据手段来逐一破解。譬如长春就是这样一座城,吉林大学等大学生诗歌创作群体及其毕业后的持续活力,由此形成的诗意氛围、高比例的诗歌纯度,使得长春在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称其为中国当代诗歌重镇,毫不为过。呈现在眼前的这部诗丛,就是一份出色的案例和证明。 吉林大学第七学生宿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以吉林大学涌现出来的一批学生为突出代表的长春高校诗歌创作群体,他们有深刻影响力的、持久的创作生涯,为长春注入了经久不衰的艺术基因和特殊的文化气质,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诗歌不是别的,而是形而上之思的载体。这是吉大诗歌创作群体的一个共识和第一偏好。对诗歌精神的形而上把握近乎本能,将其始终置于生命与世俗之上,成为信仰的艺术表达,或其就是信仰本身,在这一点上从未动摇和妥协,从未降格以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纯粹。 吉林大学文科楼 是的,正是这种高度精神化的纯粹,对艺术信仰的执念,对终极价值不变的关怀,成为吉大诗人的普遍底色。几十年来诗坛流变,林林总总的主张和派别逐浪而行,泥沙俱下。大潮退去,主张大于作品,理论高于实践的调门,剩下的诗歌精品又有几多?但是吉大诗人似乎一直有着磐石般的定力,灵魂立于云端之上,精神皈依于最高处,而写作活动本身,却低调而日常化。特立独行的诗歌路上,他们始终有一种忘我的天真和浑然,身前寂寞身后事,皆置之度外。“我把折断的翅膀/像旧手绢一样赠给你/愿意怎么飞就怎么飞吧/你是我变成的另一只蝴蝶/是一个跌倒者加入了另一种力量的奔跑”(徐敬亚《我告诉儿子》)这是一种怎样不懈的坚持啊!但是对于诗人来说,这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当苏历铭说:“不认识的人就像落叶/纷飞于你的左右,却不会进入你的心底/记忆的抽屉里,装满美好的名字”(苏历铭《在希尔顿酒店大堂里喝茶》),这并不只是怀旧,更是对初心的一种坚守和回望。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艺术家的虔诚,甚至不是他自己刻意的选项,而是命运使他不得不如此。虔诚,对于信仰与初心的执念,是上苍的旨意,和缪斯女神在茫茫人海中对诗人的个别化选择,无论这是幸运,还是一种不幸。不虚假,不做作,无功利之心,任凭天性中对艺术至真至纯的渴念的驱策,不顾一切地扑向理想主义的巅峰。诗歌,是他们实现自我超拔和向上腾跃的一块跳板。吉大诗人们,就是这样的一群。 左起:徐敬亚、兰亚明、邹进、王小妮、吕贵品、白光 诗歌在时代扮演的角色,经历着起起落落,当它被时代挤压到边缘时,创作环境日趋逼仄,非有对艺术本体的信仰和大爱,是不可能始终如一,一路前行的。吉大诗人从无气馁,而是更深沉、更坚韧,诗歌之火,依然燃烧如初。当移动互联网带动了诗歌的大范围传播,读诗、听诗和诗歌朗诵会变得越来越成时尚风潮的时候,吉大人也未显出浮躁,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着不变的步伐,从容淡定,一如既往。这从他们从未间断的绵长创作历程中看得出来,并且是写得越来越与时俱进,思考和技艺越来越呈现为纯熟,作品的况味也越来越复杂和丰厚。王小妮、吕贵品和邹进等人,笔耕不辍四十年,靠的不是什么外在的、功利化的激情,而是艺术圣徒的禀赋,这里且不论他们写作个性风格的差异。徐敬亚轻易不出手,但是只要他笔走龙蛇,便在诗坛掀起旋风,无论是他慧眼独具的诗论,还是他冷静理性与热血澎湃兼备的诗作。苏历铭作为年龄稍小些的师弟,以自己奔走于世界的风行身影,撒下一路的诗歌种子,其所经之处,无不迸射出诗歌光辉,并以独一无二的商旅诗歌写作,在传统诗人以文化生活为主体的诗歌表现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表现领域,成为另一道颇具前沿元素的崭新艺术景观。他从未想过对诗歌予以放弃,相反,诗歌是他真切的慰籍和内心不息的火焰。他以诗体日记的特殊方式,近乎连续地状写了他所经历的世事风雨,和在内心留下的重重波澜。所以,在不曾止息的创作的背后,在不断贡献出来的与时俱进的诗境和艺术场域的背后,是吉大校友诗人们一以贯之的虔敬。这种内驱力、内在的自我鞭策,从未衰减分毫! 吉林大学北极星时期的诗人们 吉大校友诗人的写作,在总体上,何以能如此一致,把诗歌理解为此生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不含杂质?恐怕只能来自于他们相互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诗歌准则,在小我、大我和真我之间,找到了贯通的路径,可以自由穿梭其间。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是吕贵品眼下躺在病床上,仍然以诗为唯一生命伴侣,每日秉笔直抒胸臆,在他心中,诗在生命之上,或与生命相始终。在诗歌理念上,他们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主观意象的营造,化为客观对象物的指涉,主观体验化为可触摸的经验,经验化为细节、意象和场景,服从于诗人的内心主旨。沉下身子的姿态,最终是为了意念和行为的高蹈,就像东篱下采菊,最终是为了见到南山,一座精神上的“南山”。 左起:包临轩、苏历铭、李占刚、任白 但是在写作策略上,吉大诗人则又显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这可称之为复调式写作、多声部写作。在他们各自的写作中,彼此独立不羁,他们各自的声音、语调、用词、意境,并不相同,却具有几乎同样不可或缺的个性化地位,这是一个碎片式的聚合体。不谋而合的是,他们似乎都不喜欢为艺术而艺术,而艺术之背后的玄思,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构建,对诗歌象征性、隐喻性的重视,似乎是他们共通的用力点和着迷之处。他们从不“闲适”和“把玩”,从不裝神弄鬼,也不孤芳自赏地宣称“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对“以译代作”的所谓“大师状”诗风,从来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他们的写作,却天然地具备知识分子化写作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独立自为地去揭示生活与时代的奥秘与真相,发掘其中隐含着的真理和善。这一切,取决于他们身后学理的、知识结构的深层背景,取决于个体的学识素养和独到见地。他们的写作,饱含着悲天悯人的基本要素,思绪之舟,渡往天与人、人与大地和彼岸,一种无形的舍我其谁的大担当,多在无意间,所以想不到以此自许和标榜。例如所谓“口语化”写作,是他们写作之初就在做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他们那里,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滑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lanhuaa.com/mlhzp/6246.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22种喜阳花卉不怕烈日,夏天养护毫无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