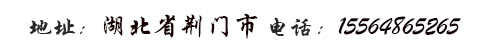离船上岸
|
离船上岸 文/茱帕·拉希里 译/施清真 她再一次为到罗马的原因而撒了谎。今年秋天,一笔研究基金减轻了她在卫斯理学院的教学负担。海玛不是因为任何公事而来意大利,只是为了好好享用同事在犹太区空着的公寓。她编了某个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古典文学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奈文和她爸妈都没有多问。对他们来说,她的学术生涯带着神秘色彩,令人敬佩,却跟他们不相干。重要的是,她拿到了博士学位,找到一份有机会晋升为终身职业的教职。她那位同事吉欧梵娜替海玛在美国学院办了使用图书馆的特权,给了她几个在罗马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十月份,海玛收拾衣物和笔记本电脑,以一个临时编出来的休假当做借口,漂洋过海来到罗马。圣诞节之前,她将前往加尔各答,她爸妈在马萨诸塞州住了一辈子后,即将返回加尔各答,她一月也将在那里与奈文成婚。 时值十一月,离感恩节还有一星期。她想想这学期错过了什么,眼前却只浮现卫斯理校园里光秃秃没剩下半片叶子的树木。沃班湖湖面已有几处结冰,她的学生们正与《韦洛克拉丁语教程》奋战,诵读着:idfactumessetumnonnegavit。夜色悄悄穿过窗户,缓缓潜入教室内。在罗马,树木也开始掉叶子,一堆堆黄澄澄的叶子堆积在台伯河的两侧。但白天让人感觉疏懒,天气温暖得让人披件小外套就可以上街走走,海玛每天吃午饭的那家餐厅,户外的露天座位依然人满为患。 餐厅离吉欧梵娜的公寓只有五分钟路程,旁边就是奥塔维亚拱廊。她当然可以试试其他几百家餐厅,也可以吃吃其他几百种不同做法的奶酪黑胡椒意大利面、奶油培根意大利面以及油炸朝鲜蓟,但她只去过几家不同的餐厅,每次不是对于食物大失所望,就是因为自己一口差劲意大利语而慌张失措。因此,她持续光顾这家她已熟悉、再也没有人过来问话的餐厅。在这家餐厅里,服务生已经知道帮她送上一瓶气泡矿泉水和半升白葡萄酒,迅速拿走第二套餐盘。他们让她静静阅读她带来的书,但她大多只是坐着观赏拱廊的遗迹,看着围上鹰架的残破廊柱和一块块巨石的庞大山形墙。衣着光鲜、喋喋不休的意大利人看也不看就穿过拱廊,观光客则停下来低头看看挖掘工作,然后继续前往马塞勒斯剧院。拱廊前方有个小广场,根据海玛勉强翻译出来的石碑,一九四三年十月间,一千多名犹太人曾在这里被驱逐出境。 她不能说是她发现了这家餐厅。多年前也就是她第一次撒谎来到罗马时,她曾和朱利安在这里吃过一顿饭。她原本没有打算再度光顾,但刚刚抵达罗马,因为时差而睡不着,出去在吉欧梵娜的公寓附近找东西吃,走着走着竟看到了这家餐厅。当年她偷偷陪着朱利安一起来,依然相信他迟早会离婚。那时是五月,罗马市区挤满了人,天气已经热得让她带来的衣服无法穿,她和朱利安住在竞技场后面的一家旅馆里,他将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文来自他以前一篇关于佩特罗尼乌斯的研究报告,这回旧瓶装新酒,重新发表了其中一章。在正常状态下,海玛也许也会发表论文,她就是这么跟爸妈说的,而他们也没有多问。但她刚刚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决定休息几个月。 海玛之前只到过罗马一次。那时她刚从布林莫尔学院毕业,跟一位女性朋友一起造访罗马。两个主修古典文学的女孩兴致盎然地从一个景点走到另一个景点,翻译碑铭,靠着意大利三明治和冰淇淋雪糕维持体力。那个首度造访罗马的旅程,令海玛永远难忘,但和朱利安同游的那一趟却是一堆什么都堆砌不成的零星记忆。她记得坐在一群在她脚边跳跃的褐色小鸟中间,跟他一起在旅馆的屋顶上吃早餐,两人在耀眼的蓝天下享用新鲜的瑞可达乳酪、熏肉火腿以及烟熏腊肠。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大早就要吃这些咸渍、油亮亮的熏肉,却始终无法抗拒。她记得旅馆房间有张大床,贴着粉红色斜纹布壁纸,朱利安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跟在佛蒙特州邓莫尔湖的太太和女儿们问好。朱利安的家人们每年夏天总是到邓莫尔湖度假。在那段婚外情当中,他们很多时候都在饭店和汽车旅馆的房间碰头,朱利安偏爱北大西洋海岸边的小旅馆,而不是海玛在纽约市立大学读研究生期间跟其他研究生共租的公寓。他们也绝不可能在朱利安位居阿默斯特的家中见面,就连他们第一次约会也是在旅馆碰头:她系里邀请朱利安前来演讲,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后,他邀她回到马克旅店小酌。 奈文绝对不会来罗马。订婚前,他们总共只相处了三个周末,其间还相隔了好几个月。奈文每次都从密歇根过来找海玛,两人中规中矩地游览波士顿,一起逛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会和吃晚餐。第二个周末时,他在她家门口亲吻她道晚安,然后回到他的朋友家休息。他跟她承认以前有过一些情人,但对自己未来的太太却相当老派。她已经三十七岁,却被当成少女般来追求,让她很感动。她直到读了研究生才交男朋友,而到了那个时候,她的年纪已经太大,男人们已不再如此慎重地追求她。 在罗马时,她与奈文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络,他们通了几次电话,谈话中尽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无任何两人共有的过去。奈文正计划果阿的蜜月之行,他们聊到此事,一起商量哪家度假酒店比较好。她不想念他,但期盼跟他在加尔各答结婚,然后一起搭飞机、赶在卫斯理学院开学前回家。奈文是她爸妈口中所谓的“非孟加拉人”,也就是说,他来自西孟加拉之外的印度省份。他爸妈是住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旁遮普人,奈文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也是个教授,原本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物理,但麻省理工学院已经答应秋天起聘用他,所以他将搬到马萨诸塞州跟海玛在一起。 她拒绝承认这是一场媒妁之言的婚姻,但心里明白的确是。虽然她比她爸妈先见到奈文,但他们却替她找到了他。爸妈问海玛说奈文可否打电话给她,多年以来,她拒绝了同样要求,始终相信朱利安会离开他太太,不过这回她总算同意。她生性害羞,而且过于投入工作,没时间理会男人,所以她爸妈以为她没有男朋友。她三十五岁生日时,她妈妈甚至问她是不是比较喜欢女人。这些年来,他们始终不知道她有个男朋友,更别提对方是个有妇之夫。即使当她在牛顿找房子,即使当她在那份总是多留下另一个签名空格的合约上单独签上自己姓名,她始终相信自己迟早会把朱利安的名字加上去。但最后她却不情不愿地步入中年,身边没有先生,也没有小孩,如今爸妈住在世界的另一端,她却拥有一个家,下雪天得自己铲雪,账单来了得自己付贷款。虽然她已向自己、爸妈和每一个人证明自己做得来这些事情,却不愿意永无止境地过着这种生活,因此,她才接纳奈文。 打从一开始,大家就假设只要奈文和她喜欢对方,而且合得来,他们就会结婚。经过了多年跟朱利安的种种不确定,海玛觉得这种假设格外令人心安。她以前看不起这种爱情观,现在却深深受到吸引,正如当年朱利安吸引了她。基于这种心态,她觉得奈文很顺眼,也喜欢上他那双清澈的褐眼,狭长的棕色脸颊以及让他看起来沉稳的黑色小胡子。认识奈文之后,朱利安再也没有突然来访,再也没有那些下午忽然响起、毁了她剩下大半天的门铃声,她再也不必等着情况改观。他们相恋了将近十年,仅仅一个电话就结束了一切。“我订婚了,快结婚了。”朱利安最后一次想要安排两人一起度过周末时,她在电话里这样告诉他。他听了之后,指责她欺骗他,骂她冷酷无情,然后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如今,她身处这个经历了很多时代的城市,各个时代好像派对上挤在一起的宾客一样毗邻而立。她摆脱了他们两人,也摆脱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她生平第一次单独出国,身边只有工作,心里明白她的单身生活即将告一段落。她珍惜这段离群索居的日子,毫不费力地一头栽进寂静的日常生活。晚上洗完澡后,她在吉欧梵娜房里的床上沉沉入睡。这房间虽然不大,但天花板却极高,庞大的百叶窗为她遮挡了阳光,但隔绝不了种种声响:阿雷努拉街上摩托车和汽车穿梭而过,各家商店拉起铁门做生意,街上不停传来单调的救护车声,但奇怪的是,她听了却感到心安。罗马的某些方面让她想起加尔各答:陈旧雄伟的建筑物,交通繁忙到难以过马路的主要街道。罗马就跟她童年时去过的加尔各答一样,从一方面来说,她对这个城市熟得不得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却一无所知——这是一个让她深深投入却又将她拒于千里之外的地方。她熟悉古罗马的语言,历代统治者和作家以及城市的兴亡史,但她只是一个在意大利的普通观光客,除了正在柏林休假研究的吉欧梵娜,她没有任何罗马朋友。 每天早上,她泡杯意大利浓缩咖啡,热了牛奶,在方块吐司上抹上果酱。八点前,她已经坐在吉欧梵娜的桌前,桌上现已堆满海玛的书、笔记本、笔记本电脑以及拉丁文语法字典。虽然市内有成百件她可做的事,或是可看的物,但直到下午一点前,她每天遵循同样的作息,这是她生活的主轴,多年以来,她始终以此为支柱。她现在是教授了,她那篇关于卢克莱修的论文已经装订出版,也已悄悄得到赞誉,但基于工作所需,她还是必须独自在书桌前坐上好几小时,而她依然觉得这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令人满足。她从八年级就迷上拉丁文,每行文字都是个谜团,等着她找出意义。这些年来她所积累的知识,那些常驻在她脑海中的古代文字、变格和语意,让她为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注入生命,感觉非常神圣。 现在她的研究重点是伊特鲁里亚人。几个月前,她在波士顿听了一场演讲,演讲中提及伊特鲁里亚人在维吉尔作品中的事迹,促使她一头钻入研究这个发迹于罗马之前的神秘文化。说不定伊特鲁里亚人是从小亚细亚流浪到意大利中部,其文化兴盛了四个世纪,而且统治了罗马一百年,然后销声匿迹。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已不存在,语言也无人通晓,最重要的遗迹是坟墓和埋藏在内的物品,比如珠宝、陶器以及陪葬者的武器。她正在研读关于“脏卜师”的文献,也就是从动物内脏、闪电、怀孕妇女的梦以及鸟类飞行当中预卜神明旨意的占卜师。回到卫斯理学院后,她想召开一场专题研讨,阐释伊特鲁里亚文化对于罗马古代器物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说不定根据她的研究着手进行第二本书。她已经去了梵蒂冈参观格里高里博物馆的伊特鲁里亚收藏品,也去了一趟朱里亚庄园博物馆。她正仔细检阅西塞罗、西尼加、里维和普利尼的作品,阅读神秘学者暨参议员菲古卢斯的部分著作,用电脑做出摘要,标出许多读过的书籍。 因此,海玛还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也没有联络吉欧梵娜的朋友们。吉欧梵娜向她保证,他们一定乐意请她喝咖啡,或是开车带她去蒂沃利和奥斯蒂亚,但她情愿一个人过日子,白天阅读、做研究,中午到奥塔维亚拱廊旁边吃午餐,下午在各个教堂游览,沿着狭小的巷道漫步,巷道黑暗拥挤,却一路延伸到光线夺目的巨大广场。她到哪里都步行,几乎从不借助公共汽车或是地铁。晚上她回家休息,在家准备食物,边吃简单的晚餐边收看意大利电视节目。晚上单独出去,感觉怪怪的,自己在外吃晚饭,也比独自吃中饭更不自在。她跟朱利安在一起的那些年,即使只有她一个人,男士们也感觉到她的芳心已有所属,仿佛她是一部疾驶而过、休息灯信号已经亮起的出租车,不会停下来关照他们。现在虽然已经订婚,她却依然察觉罗马男士们盯着她看,有时还对着她大叫。虽然他们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lanhuaa.com/mlhzp/6576.html
- 上一篇文章: 东航南航大量取消23月日本线,国航宣布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